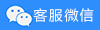紡織產業發展不可忽視中國優勢
紡織工業屬于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紡織業取得了長足發展,紡織服裝出口占全球出口總額三分之一以上,是全球紡織服裝制造和出口的第一大國。在這個過程中,紡織產業經歷了艱難歷程,上世紀90年代實施的棉紡織壓錠政策,與今天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類似,或者說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探索與實踐。
紡織服裝產業是中國一個重要的優勢產業。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紡織行業需求發生根本性逆轉,15年中我國棉紡錠增加了3倍,紡織服裝工業迎來了歷史性的高速發展,當初的產能過剩邏輯則陷入了尷尬,對實行壓錠政策出現了一些新的討論。總量控制政策、產業援助政策,以及產業區域政策等,如何在全球化條件下制定與實施,成為需要進一步研討的話題。
根據2019年底發布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在制造和批發零售兩個領域,紡織服裝產業有121萬家法人企業,擁有資產9.37萬億元。2018年的營業收入達到12.7萬億元,超過當年中國GDP總額的14%,是僅次于電子信息產業的中國第二大產業部門。
紡織服裝行業的法人企業直接從業人員多達1563.6萬人,加上個體工商戶和農業領域的棉農,估計該行業直接雇傭的人員為2500萬人,直接影響大約2000萬個家庭,也就是8000萬到1億人的生計。
今年全國兩會召開期間,各類涉及民生發展的議題頻上熱搜,引起大家共鳴。全國人大代表陳麗芬提出,要進一步打造產業用紡織品國際競爭新優勢。她建議,為完善相關政策措施,引導和支持產業用紡織品行業發展,一是要提升產業用紡織品在行業分類中的地位,二是要成立全國產業用紡織品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三是要成立產業用紡織品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
事實上,作為戰略性新材料的組成部分,產業用紡織品已經成為我國工業體系中最具活力的領域之一,在雙循環發展格局下彰顯出巨大發展空間。未來,紡織工業需面對要素成本上升和競爭優勢衰減問題,產能過剩問題將逐步凸顯,為確保就業穩定及保持我國整體產業優勢,有必要研究新形勢下的相關政策與措施。
都市圈中的核心圈,各種類型的能夠較好滿足城市生活需要的工業及生產性服務業以各種形態存在。盡管傳統制造業轉型步伐不斷推進,服務經濟持續發展,但都市工業仍在都市經濟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大城市中分布了“大規模”的傳統制造業,這類企業產品技術含量不高,但職工人數多、占地面積大。以上海紡織工業為例:1991年底,上海國有紡織服裝企業494戶,在職職工53.5萬人,退休職工28萬人,工廠占地818萬平方米,固定資產原值75億元,棉紡能力241萬錠,職工人數超過1萬人的企業有好幾家。隨著城市化進入成熟階段,以及效益更好的替代產業相繼出現,這些紡錠在上海市區實際上難以生存。
隨著中心城市產業結構調整的深入推進,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中心城市輻射功能日益凸顯。都市產業結構的演進,一方面,要求傳統制造業主動實行退出和收縮;另一方面,城市工業需要提高技術水平,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另外,適應市場快速變化的都市型工業同樣具有生存空間。
紐約現有產業結構中,盡管制造業比重不高,但仍保留服裝、印刷和食品等典型的都市型工業。其中,服裝加工約占制造業增加值和就業總人數的1/3左右,并以生產高端品牌和奢侈品牌服裝為主,使得紐約保持了全球時尚產業長盛不衰的領先地位。
紐約服裝加工業對投資仍具有一定吸引力,服裝加工曾經是紐約最具代表性的制造產業之一,長期以來為紐約提供了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紡織及服裝產業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壓力下進行了結構調整,產業發展呈現出品牌產品差異化、企業規模微型化、生產技術柔性化以及貿易政策自由化等諸多特征。同時,由于產業鏈全球化和離岸外包業務的快速發展,新世紀的前10年,美國國內服裝制造業規模產生一定程度的萎縮,紐約服裝制造業盛景不再。
隨著美國大力實施制造業回歸戰略,紐約服裝產業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回流跡象。數據顯示,2016年紐約服裝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達到3億美元以上,比2013年增加了5%;2017年全行業產值達到125億美元,出現了自1998年以來的首次增長。包括男士定制服裝Brooks Brothers、運動時尚品牌American Giant、女裝品牌Karen Kane等在內的美國服裝企業都增加了“回岸”采購本土服裝制造份額,主要原因包括海外成本上升、更好地進行質量控制、更靈活組織生產、更短交貨期。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戰略使得美國服裝制造業在高端品牌領域具有了更大競爭優勢。(作者系華夏幸福研究院研究員)
全球化下的中國紡織產業
紡織服裝產業是中國一個重要的優勢產業。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紡織行業需求發生根本性逆轉,15年中我國棉紡錠增加了3倍,紡織服裝工業迎來了歷史性的高速發展,當初的產能過剩邏輯則陷入了尷尬,對實行壓錠政策出現了一些新的討論。總量控制政策、產業援助政策,以及產業區域政策等,如何在全球化條件下制定與實施,成為需要進一步研討的話題。
根據2019年底發布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在制造和批發零售兩個領域,紡織服裝產業有121萬家法人企業,擁有資產9.37萬億元。2018年的營業收入達到12.7萬億元,超過當年中國GDP總額的14%,是僅次于電子信息產業的中國第二大產業部門。
紡織服裝行業的法人企業直接從業人員多達1563.6萬人,加上個體工商戶和農業領域的棉農,估計該行業直接雇傭的人員為2500萬人,直接影響大約2000萬個家庭,也就是8000萬到1億人的生計。
今年全國兩會召開期間,各類涉及民生發展的議題頻上熱搜,引起大家共鳴。全國人大代表陳麗芬提出,要進一步打造產業用紡織品國際競爭新優勢。她建議,為完善相關政策措施,引導和支持產業用紡織品行業發展,一是要提升產業用紡織品在行業分類中的地位,二是要成立全國產業用紡織品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三是要成立產業用紡織品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
事實上,作為戰略性新材料的組成部分,產業用紡織品已經成為我國工業體系中最具活力的領域之一,在雙循環發展格局下彰顯出巨大發展空間。未來,紡織工業需面對要素成本上升和競爭優勢衰減問題,產能過剩問題將逐步凸顯,為確保就業穩定及保持我國整體產業優勢,有必要研究新形勢下的相關政策與措施。
都市圈也需都市工業
都市圈中的核心圈,各種類型的能夠較好滿足城市生活需要的工業及生產性服務業以各種形態存在。盡管傳統制造業轉型步伐不斷推進,服務經濟持續發展,但都市工業仍在都市經濟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大城市中分布了“大規模”的傳統制造業,這類企業產品技術含量不高,但職工人數多、占地面積大。以上海紡織工業為例:1991年底,上海國有紡織服裝企業494戶,在職職工53.5萬人,退休職工28萬人,工廠占地818萬平方米,固定資產原值75億元,棉紡能力241萬錠,職工人數超過1萬人的企業有好幾家。隨著城市化進入成熟階段,以及效益更好的替代產業相繼出現,這些紡錠在上海市區實際上難以生存。
隨著中心城市產業結構調整的深入推進,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中心城市輻射功能日益凸顯。都市產業結構的演進,一方面,要求傳統制造業主動實行退出和收縮;另一方面,城市工業需要提高技術水平,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另外,適應市場快速變化的都市型工業同樣具有生存空間。
紐約服裝制造業盛景不再
紐約現有產業結構中,盡管制造業比重不高,但仍保留服裝、印刷和食品等典型的都市型工業。其中,服裝加工約占制造業增加值和就業總人數的1/3左右,并以生產高端品牌和奢侈品牌服裝為主,使得紐約保持了全球時尚產業長盛不衰的領先地位。
紐約服裝加工業對投資仍具有一定吸引力,服裝加工曾經是紐約最具代表性的制造產業之一,長期以來為紐約提供了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紡織及服裝產業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壓力下進行了結構調整,產業發展呈現出品牌產品差異化、企業規模微型化、生產技術柔性化以及貿易政策自由化等諸多特征。同時,由于產業鏈全球化和離岸外包業務的快速發展,新世紀的前10年,美國國內服裝制造業規模產生一定程度的萎縮,紐約服裝制造業盛景不再。
隨著美國大力實施制造業回歸戰略,紐約服裝產業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回流跡象。數據顯示,2016年紐約服裝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達到3億美元以上,比2013年增加了5%;2017年全行業產值達到125億美元,出現了自1998年以來的首次增長。包括男士定制服裝Brooks Brothers、運動時尚品牌American Giant、女裝品牌Karen Kane等在內的美國服裝企業都增加了“回岸”采購本土服裝制造份額,主要原因包括海外成本上升、更好地進行質量控制、更靈活組織生產、更短交貨期。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戰略使得美國服裝制造業在高端品牌領域具有了更大競爭優勢。(作者系華夏幸福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