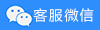美機MAQI,琦星電控操作說明
美機MAQI,琦星電控操作說明
在縫紉機行業奮斗了一輩子,65歲的卓瑞榮還在為最終的放手而奮力一搏。
5月中旬,卓董事長剛從臺灣地區返回嘉興,就被我們“抓”住。經歷了三年疫情的洗禮,再加上眾多同行的“圍追堵截”,堅持不向“價格戰”低頭的星銳縫紉機(嘉興)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星銳)境況如何?被稱作“技術狂人”的卓董又有哪些新動作、新思考?
星銳董事長卓瑞榮
從2007年到嘉興創業至今,卓瑞榮在15年里一直以一種“卓爾不群”的姿態,做了很多令人當時不解、事后卻恍然大悟的事情。
比如,他沒有直接從臺灣地區熟門熟路的供應商手里采購零配件,而是花了十多年在大陸培育出一個精品零配件供應鏈。中間的勞心費力,甘苦自知。
再比如,他始終堅持把星銳的產品售價定位在合理水平、并給到代理商足夠的利潤,而且還堅持現金提貨,絕不會為了搶占客戶而允許欠賬、賒賬。
這些看似不夠明智、不夠靈活的做法,背后彰顯的是卓瑞榮對工匠精神、商業倫理和長期主義的追求。
卓瑞榮當選嘉興市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第十屆常務副會長
這種追求可以具化為“三品原則”:品質、品牌和品格。品牌的基礎是品質,企業文化的靈魂是品格。
他說,“我現在開會還在講一個觀點。30年前日本出口的縫紉機,只要開箱就要收開箱費,其實就是保證機器拿出來品質沒問題。我就跟裝配部負責人講,日本人能做到每一臺機器的品質保證,我們也要做到;每一臺機器出去,就要保證品質,品質沒有保證就重新再來,這才是所有的縫紉機(品牌)應該做的。”
從17歲入行到自己創業再到來大陸創辦星銳,卓瑞榮將“品質”視為其一生信仰的價值指針。他的社會責任意識、誠信主張和對不走捷徑的堅守,都給“星銳”這個品牌注入了積極正向的品格。
星銳縫紉機(嘉興)有限公司
從零件設計、制造中錘煉工匠精神
都知道卓瑞榮是設計和制造零件出身,但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功力”是怎么煉成的。
卓瑞榮在家里十三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我哥很聰明,我自己就很笨,那怎么辦呢?當然是當學徒了。”
他早期去高林當學徒,師傅不肯教。只好做個有心人、勤快人。師傅要什么工具,還沒開口,他就遞上去了,然后看一次就能學會。還有,高林有個模具車間,里面的模具每年都需要去擦一次。
“里面很悶熱,但我總是沖第一”。他說,不管有多少模具要擦,他就一個一個地看,研究人家模具是怎么做的。就這么經過一次、兩次、三次,卓瑞榮對各種零部件的構造入腦入心,后來他做的模具就是跟別人的不一樣。別人一般要學三年六個月才能當師傅,他只用兩年就做到了。
每次聊起這些往事,他就很開心,也很感慨。凡事最怕“用心”二字。用心學習,專注設計,精益制造,這就是工匠精神。
卓瑞榮說,2007年他一個人來大陸,從最早“一個零件不能用,到現在98%的都可以用”。有臺灣朋友跟他開玩笑,說“大陸的零件現在越做越好,都是你的問題”。他說:你們不對,不是我的問題,你們之前做得好,不也是從人家手里學來的嗎?
在星銳的推動下,中國縫紉機零部件品質越來越好
他認為,大陸的零件不是不能做精準,而是需要三個條件。一是要給零件廠商合理的價格,二是健全零件檢測機制,三是要從零件的重要部位開始提高精準度。“零件做不好,機器怎么能做得好?大陸很多零件廠家也意識到要注重質量,愿意跟我合作。有的零件甚至做了一年,做了20幾次都被我打回去,他們仍然愿意嘗試。” 他說,現在大陸的零部件(品質)已經不亞于臺灣地區的零件了。
星銳的產品品質一直備受業界贊譽
善助人者天助之。有時候做“傻”事、做難的事需要堅持和信仰,但事后看就是事半功倍。星銳的繃縫機、拼縫機15年前就被國內同行模仿,而且產品售價比仿造品高很多,但就是屹立不倒,口碑極佳,鐵粉眾多。
鏈家前董事長左暉說過一句話:“我們這個時代企業經營者的宿命,就是要去干煙花背后的真正提升基礎服務品質的苦活、累活。干難的活,干累的活,干慢的活。”
從這個意義上說,卓瑞榮為中國縫制機械行業的進步做了一件大好事。沒有他的堅持、“挑剔”和背后推動,中國大陸零部件整體水平的提升,可能還要花更長時間。
堅持走質優價高路線
卓瑞榮真正開始介入縫紉機,是早期在臺灣地區跟徐石淵先生合伙創辦星菱的時候。那時候他是董事長,徐石淵是副董事長。八年半之后,兩人拆伙,卓瑞榮離開星菱并創立了星銳。
他一開始就做繃縫機,從787開始研發制造,然后是720、730、740、780、750、760、2790一路做下來,繃縫機幾乎所有的產品體系都覆蓋到了。
他說,之所以做繃縫機,是當初就認為:以前的服裝縫制,平均下來梭織占7成、針織占3成,但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經反過來了,針織占7成,梭織占3成。“針織用什么機器?就是包縫和繃縫。包縫我是做不了,不是技術上做不了,而是需要大投入、而且價格拉不上來,所以只能做繃縫機。”
星銳縫紉機一直堅持走質優價高路線
卓瑞榮的經營理念之一,是不做大路貨、不打“價格戰”,堅持走質優價高路線。15年前,一個土耳其朋友到他的臺灣公司考察,通過翻譯問他,說你為什么不做四針六線?卓瑞榮說四針六線只能縫內衣褲和潛水衣,其它的做不了,所以機器需求量很少。土耳其人說不是,現在四針六線已經應用到針織領域,他自己買30臺,要拿現金去大和等三個月才拿到貨。“我就說,這種機器這么搶手,不做才怪。”
然后他買了一臺四針六線拼縫機擺在辦公室里研究。他了解得很仔細,用什么螺釘,為什么要用這個螺釘,螺釘的重量有多少等等,他都認真分析過。然后用他過硬的零部件設計功底,將里面最核心的五個零件一一破解。
比如,壓腳上有兩個月亮形的零件,熱處理之前要把它們鉚起來,但經過熱處理會變形影響精準度,怎么辦?他就用精密鑄造做出來,結果兩三年后日本大和、飛馬也開始采用類似精密鑄造的方法。
他仿的四針六線,幾乎已經脫胎換骨。“當我的FW740-TA、FW740-TJ和FW740-TD制造出來的時候,質量已經不輸給日本產品;現在740已經從TA升級到TB, 并且有一些專利已經超過日本品牌了。所以我敢說自己的四針六線已經不亞于大和、飛馬了。”
星銳的拉鏈縫合機也很有名。這得益于他最早在1982年創業時就做拉鏈針鎦、針板組。1997年,他研發出全球第一款拉鏈縫合機HR-3000,后來又有了HR-3200,星銳還要繼續把拉鏈機升級到3500、3600、3700,連日本YKK都跟他們采購了兩三千臺。現在中國大陸的拉鏈廠,用的90%的縫合機都是星銳的。
浪莎襪業使用的星銳縫紉機
青島文森使用的星銳縫紉機
世上本沒有完美,但最難得的是追求完美的心。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否則追求卓越和成為卓越就只會是空談和幻想。
15年前就看到縫紉機未來的30年
2008年在嘉興創辦星銳時,卓瑞榮就看到了未來30年縫紉機發展的大體脈絡。
他說,“當時我就看到30年后的縫紉機一定會走向半自動化、自動化和智能化。而如果要做到自動化和智能化,最重要的是機頭要穩定。所以現在我們很多的自動化、半自動化設備,機頭都用日本品牌的,不是兄弟就是重機或飛馬,這就像被人家掐著脖子一樣。”
星銳原本準備在2018年投入自動化設備研發,卓瑞榮也為此做過深度思考和周密準備。他說,自動化設備所有的動作設計,一定需要軟件設計和結構設計兩個團隊才能實現。但因為三年疫情下來,再加上一些客觀原因,這件事就一直耽擱下來。
如今,星銳同樣面臨著新老一代交接班。擔任星銳總經理的卓立偉正努力為接班做準備。他隨父親在大陸打拼了多年,2011年到嘉興公司后,除了業務、財務和研發之外,其它部門都歷練過一番。現在,他對技術表現出濃厚興趣,也在跟著父親搞研發。卓瑞榮說,現在不僅要扶他上馬,還要幫他鋪好路。除了繼續狠抓產品品質之外,去年年底,他還革新了公司銷售方式,親自下場抓業務,包括大力培養業務員,夯實售后服務體系等等。
星銳總經理卓立偉正努力為接班做準備
同時,他也時刻關心著中國縫制機械行業的發展。他說,要在中國大陸生根,就要以品質為首。不管怎樣,中國的縫紉機一定要崛起,也一定會崛起,不能再以低價、低質來競爭。“如果不提升質量,最后你的產品會被人家拋棄。”
據他觀察,一些成衣廠,尤其是一些大型成衣廠已經不再使用大陸生產的設備。一個原因是歐美抵制中國制造引起的;另一個原因,還是因為質量。“現在這些大型成衣廠選擇機器又慢慢回歸到重機、兄弟、大和、飛馬等國外品牌。這是我收集到的信息,到底對不對,時間會慢慢來印證。”
他不久前回臺灣地區開會,就有同行希望星銳也做低價位產品。“我就跟他說,我做不了,要在大陸生存,只能品質好、價格合理才行得通。” 在他看來,如果國產品牌的品質再不升級的話,未來很可能只能在國內生產、國內銷售。可是再過十年,如此低質低價的產品,還能生存多久呢?
星銳的產品15年前就被同行仿造,卓瑞榮對此抱著自信、樂觀的態度。他說,如果你的產品沒人仿了,這其實對它來說是一個警訊。不過作為一個研發者,他當然不喜歡侵犯人家的專利,也不喜歡人家侵犯他的專利。但在現實情況下,特別是專利到期之后,被仿是無法避免的問題。
星銳在嘉興深耕15年,贏得社會各界認可
“我們怎么辦?一是確保質量,每一臺機器出去都要保證品質,這是我們的根本。二是要不斷升級,比如繃縫機,我們仍然還在持續研發,等到明年初又會有一款全新的繃縫機亮相。”
星銳也是靠仿造日本的機器起家,但是仿造不能侵權,用卓瑞榮的話說,“要仿,也要仿出本事,仿出水平”。因此還是要不斷創新。但是一旦要創新,一旦要注重品質,就不可避免地要拉高成本,這也是星銳為什么要賣貴的原因。
卓瑞榮看問題一針見血,也善于用未來的眼光謀劃企業發展。在他看來,其實進口縫紉機早晚都會淡出中國市場,那到時候這個空間由誰來填補呢?機會一定會留給有實力的人、有準備的人。
卓瑞榮和星銳的故事告訴我們,無論昨天的光榮還是曾經的教訓,都是今天的墊腳石,重要的是相信自我,超越自我,創新贏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