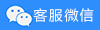杰克JACK,C6包縫機,縫紉機電腦箱維修
杰克JACK,C6包縫機,縫紉機電腦箱維修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渲染下,1851年,世界上第一臺全金屬材質的鎖式線跡縫紉機于勝家問世,并在至此之后的一百余年中見證了縫紉機產業的快速崛起。
一百年的時間,在歷史長河上僅是滄海一粟,對一個行業來說,可能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對于一個人來說,這百年必然承載了他生命的全部重量。
如果說勝家見證的是美國縫紉機的崛起,那能夠像歷史教科書般記錄中國縫紉機發展史的一個人,就是上海市縫紉機研究所高級顧問雷杰。他今年快80歲了,一輩子就做了研究縫紉機這一件事。
今年三月,我們與雷杰老師對話了近三個小時,暢談上海縫紉機工業發展史上的點點滴滴,以及他對于行業高質量發展的觀點和看法。
“全國到現在為止唯一經過大專學習的縫紉機班就是我們那一批人,兩個班,99個人。回首過去已經60年了。”這是雷杰在訪談開始后的第一句話,語氣中帶著驕傲,卻也有一絲惋惜。
1963年,上海輕工業專科學校開設機械專業縫紉機班,四年制,半工半讀。兩年的基礎和專業知識理論學習后,第三年,這99個學生便投身到了工廠實習之中,那是一個現在已經不復存在的工廠,但也是中國縫紉機工業的開山鼻祖之一——上海縫紉機一廠。
在一廠的這段實習經歷,讓雷杰接受到了與以往不同的教育,也為他以后深耕縫紉機技術工作奠定了基礎。
在縫紉機一廠,他首先接觸到了工廠工程師們根據實際工作編寫刻印的《縫紉機原理》《縫紉機加工工藝》《縫紉機加工設備》等“鄉土教材”,一個個工整的方塊字都散發著老工程師們認真的態度和嚴謹的匠心;他還接觸到了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到的縫紉機產品,上了很多加工工藝課、加工刀具課和加工設備課,感受到了機械工業的博大精深。
雷杰畢業后,正式被分配至縫紉機二廠(后更名為協昌縫紉機廠)機殼車間底板加工組當產品工,每天要完成1500個底板四周銑加工的生產指標,五個月后又被調到車間機修組學習設備修理。
他說,這段時間實際上是自己學習縫紉機以來進步最快的時期。師傅諄諄教導他:“最難的活,要敢接;最臟的活,要肯接;別人不愿意接的活,都要接。人的本領,是在不斷干活過程中學會的。”這簡單樸實的幾句話,雷杰默默在心中記了一輩子。他專心向師傅學習,苦練機修本領,不到兩年時間,終于迎來了一次有挑戰的“畢業考”。
那一晚,夢鄉中的雷杰被一位老師傅叫醒搶修一臺機器,由于他是那天唯一一位住在廠內的機修師傅,便馬上從床上爬起來挑起了重任,通宵了一晚,將長期跟師傅學習的實戰經驗和在校時刻苦學習的理論知識相結合,他第一次完全獨立成功完成了修理工作,并且謹慎細心的他,又加工了十個產品檢驗是否合格,一切處理妥當,同事們也都已經來上班了。“你修好了?”組長驚訝地問雷杰。得知了事情的全部過程后,組長便催促著雷杰趕快去休息。離開車間的雷杰臉上洋溢著藏不住的喜悅,也是這時候,他真正體會到了師傅的那句“人的本領,是在不斷干活過程中學會的。”
車間主任自然將雷杰的進步看在眼中,便將他調到了車間技術組,當車間工藝技術員,管理車間加工工藝,以及加工刀具、夾具、工具等工藝裝備。而這,也正是他漫長的縫紉機事業的開端。
車間加工工藝,是車間技術工作的核心,不僅要了解加工產品的質量要求,還要了解產品在加工過程中的加工設備、加工工藝,加工用的刀具、夾具、工具、量具等工藝裝備狀態。要求工藝技術員的知識面寬,實際工作經驗豐富,問題處理能力強。
那時,只要是廠里的人都知道,什么都能停,就是生產不能停,所以跟機器有關的事,都是大事。
雷杰回憶說:有一天快下班的時候,一把加工車殼的導架槽的銑刀壞了,倉庫也沒有備貨,工具科便連夜趕工,趕出了兩把銑刀。但當第二天早晨把刀具旋到設備上一試,卻發現刀具的螺紋標準不一樣,設備上是公制的,做出來的新銑刀卻是英制的。之前雷杰做機修時,每次深夜修完機器,總會再加工十個產品檢驗是否合格,顯然,這次工具科的同事在工作上并沒有這么嚴謹。
在旁人看來,這是一次“失誤”,或者說是不夠細心,但在雷杰看來,作為源頭的圖紙管理可能出了大問題。在詳細整理信息后他發現,車間和工具科用的刀具及設備的螺紋標準混亂,有公制的、也有英制的。如果每次加工刀具前都要確認好標準,那還不如就從源頭把刀具圖標準統一,解決生產難題,保證生產效率。
雷杰便從整個車間的所有刀具圖紙著手,將過去6套不同版本的刀具圖,統一更新為親自重新繪制矯正過的全新版本,并同時重新繪制了車間全部工藝文件的全新版本。
這次 “刀具事件”給雷杰帶來了很大影響,“圖紙管理”的概念也跟隨他到了每一個工作崗位。
因為工作努力且出色,雷杰很快被提拔為廠技術科副科長,仍主管工藝。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于是他一上任便大刀闊斧地對全廠1379道工序進行了標準化校正。他自己主起草工藝文件標準圖,發動了全廠8個車間的所有工藝員,耗時整整兩年,最終創作完成了1379版協昌縫紉機廠的工藝文件。這套工藝文件,直到協昌縫紉機廠2000年后停產前仍在使用。
當時身為廠里主管產品、工藝、標準、信息、檔案技術工作負責人的雷杰已經深深明白,縫紉機產業既是勞動密集型的,又是技術密集型的,沒有標準化的管理,這兩種特征都會受到限制。
當時許多縫紉機廠采用的管理模式都是傳統的作坊式,其一大特征就是生產技術資料基本都是靠老師傅經驗總結歸納出的一些文字資料、技術資料,這些寶貴的財富如同未經雕琢的璞玉,經過規范的技術管理整理后,才能展現出它們真正耀眼的光芒。
從上世紀90年代一直到2010年之后,雷杰連續擔任全國縫紉機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副主任、顧問。全國縫紉機標準化中心2006年所使用的《縫紉機術語》文件中,主要起草人之一也是雷杰。
1973年,“當時全國輕工部研發縫紉機底板加工組合機床自動線,主要的技術支持是大連組合機床研究所,那里能夠接觸到前蘇聯留下的一套很完整的機床設計的標準化手冊,這對于大部分技術員來說,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這項工作本來安排車間另一個老工程師去參加,但后來他身體欠佳,車間便安排了我去參加設計。”
“當時全國總共有機殼、車殼、底板加工三條自動線同時開始研發,結果,其他兩條線失敗了,其實是因為一開始設計理念有問題,所以我感覺自己的機遇比較好。”
“1983年,上海工業縫紉機廠有一個國家經委批準的引進日本‘高速平縫機產品技術及加工設備’項目。公司領導調我去擔任這個全國最大的縫紉機項目負責人,1984年后公司領導決定任命我為上海工業縫紉機廠廠長。當時廠長的選拔,是根據鄧小平同志的專業化、革命化、年輕化這三個標準進行的,我正好占了年輕化的優勢,所以從一個技術員、工程師開始,被提拔成為廠長也是我的機遇好。”
雷杰在講述自己每個人生階段的經歷時,總是提到“機遇”二字,但事實上,哪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機遇的背后其實都是天道酬勤的結果。
1973年在參與縫紉機底板加工自動線項目時,雷杰延續著自己對于標準化的堅持.由于項目非常龐大,全國有七個廠的工程師、老師傅都參與了進來,他為了盡可能減少誤差,所有圖紙都要親自校對,那時的鉛筆圖紙修改起來也非常麻煩,有時候擦掉修改還不如直接自己重畫,但他依然沒有放棄,從始至終以嚴謹的態度用整整一年的時間完成了自動線的設計工作。
1974年設計工作完成,設計組解散后,全套圖紙就被送到了生產單位,由雷杰一個人在生產工廠主持自動線試制的技術服務工作,1975年自動線制造完成拉到縫紉機二廠,也由雷杰主持安裝調試。1976年1月由于長期在自動線安裝調試,埋頭在車間近半年沒有離開工廠,再加上之前的長時間高強度工作埋下的隱患,雷杰突然胃大出血,被送進了醫院搶救,醫生的一句話讓周圍所有人很震驚了——做好心理準備,可能是胃癌。
“如果確認是胃癌,趕緊幫我處理一下,讓我出去,這樣我最后還能再處理一點事情,換一個人過去什么都不知道,等于又要重新開始了。”雷杰在被送進醫院前不久,調試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問題,他當時滿腦子還都是自動線的數字。但醫生說什么也不讓他走,因為這其實是雷杰第二次胃出血了。
雷杰只得老老實實在醫院待了一個月,好在最后排除了胃癌的可能,這才正式出院。后來的調試工作強度并不高,雷杰的身體也在這個階段得到了適當的休養。
1977年5月,輕工部前來工廠驗收項目,一次性通過。1978年“縫紉機底板加工組合機床自動線”項目還獲得全國第一次科學大會重大科技成果獎。
時任工業縫紉機廠廠長的雷杰已經38歲了,但是跟身邊50多歲的副廠長、老廠長相比,自己還是年輕的小伙子。至于他的專業水平,也是靠先前一點一滴積累出來的。
那時候的雷杰,常常留戀在縫紉機二廠工作的情景,沒有所謂的上班和下班,單身的他住在工廠、吃在工廠,有時甚至三個月、半年都不會離開工廠,并且,他很享受下班后一個人在車間的時光。沒有其他工作的影響,一個人就在空無一人的車間里,一個尺寸一個尺寸地校對,一個文件一個文件地修改。
正是這些勤奮、用心,為雷杰打下了扎實的專業基礎。后來去日本考察時,他與日本重機公司的談判,一談就是一個月,從產品討論到工藝,又從工藝討論到設備,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為后續談判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為我國的縫紉機行業爭了口氣。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用這八個字來形容雷杰再合適不過了。他在談話中間總是強調,跟他能力相當或是比他能力更強的同輩大有人在,但自己正因為有較好的機遇,才放大了自己的勤奮,收獲到了更多的成果。
從1983年開始,前前后后因為技術談判、設備驗收、組織考察等等事因,雷杰一共去了日本5次,每一次去,對他而言都是一次震撼。
他是這樣描述的:“他們的工廠雖然很小,但是管理得井井有條。比如說,重機大田原工廠的老廠長,現在已是重機公司的元老。在1938年工廠剛建立時,作為廠長的他,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檢查廁所是否干凈,因為如果連廁所都干凈了,工廠其他地方自然就不必再檢查了。檢查完廁所之后,他便會拿起掃帚親自打掃工廠門口的十字馬路,掃完后再穿著白襯衫橫躺在馬路上,一直掃到白襯衫上不會染上任何灰塵為止。”
他感嘆道:“日本同行在細節方面真是做得很好,他們的廠長以身作則這件事情也確實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來在工廠管理方面也給了我許多啟發。”
反觀國內,數十年來高速發展,行業保持著瞬息萬變、日新月異的迅猛勢頭,這確實是好事,但每經過一些階段,我們是否需要回首?是否需要從過去的路程中自省?不管是對于標準化的堅持,還是吃苦耐勞的精神,不知為何都在我們行業慢慢強大的路上逐漸弱化了。
現在看行業的發展,其實欠缺的是擁有心懷家國情懷、系統性發展的概念,以及整個行業發展的概念。七宗罪是西方傳來的說法,其中一罪便是貪婪,確實,人要戒貪是件難事,但這也是達成高質量發展必須要做的事。
“現在的人都好浮躁,我不希望大家總是在空中。我們這個行業現在真正需要好好沉下心來去討論,什么叫高質量發展。”
一百年的時間,在歷史長河上僅是滄海一粟,對一個行業來說,可能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對于一個人來說,這百年必然承載了他生命的全部重量。
如果說勝家見證的是美國縫紉機的崛起,那能夠像歷史教科書般記錄中國縫紉機發展史的一個人,就是上海市縫紉機研究所高級顧問雷杰。他今年快80歲了,一輩子就做了研究縫紉機這一件事。
今年三月,我們與雷杰老師對話了近三個小時,暢談上海縫紉機工業發展史上的點點滴滴,以及他對于行業高質量發展的觀點和看法。
縫制機械行業資深專家
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中外縫制設備》雜志顧問 雷杰
“全國到現在為止唯一經過大專學習的縫紉機班就是我們那一批人,兩個班,99個人。回首過去已經60年了。”這是雷杰在訪談開始后的第一句話,語氣中帶著驕傲,卻也有一絲惋惜。
1963年,上海輕工業專科學校開設機械專業縫紉機班,四年制,半工半讀。兩年的基礎和專業知識理論學習后,第三年,這99個學生便投身到了工廠實習之中,那是一個現在已經不復存在的工廠,但也是中國縫紉機工業的開山鼻祖之一——上海縫紉機一廠。
在一廠的這段實習經歷,讓雷杰接受到了與以往不同的教育,也為他以后深耕縫紉機技術工作奠定了基礎。
在縫紉機一廠,他首先接觸到了工廠工程師們根據實際工作編寫刻印的《縫紉機原理》《縫紉機加工工藝》《縫紉機加工設備》等“鄉土教材”,一個個工整的方塊字都散發著老工程師們認真的態度和嚴謹的匠心;他還接觸到了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到的縫紉機產品,上了很多加工工藝課、加工刀具課和加工設備課,感受到了機械工業的博大精深。
雷杰畢業后,正式被分配至縫紉機二廠(后更名為協昌縫紉機廠)機殼車間底板加工組當產品工,每天要完成1500個底板四周銑加工的生產指標,五個月后又被調到車間機修組學習設備修理。
他說,這段時間實際上是自己學習縫紉機以來進步最快的時期。師傅諄諄教導他:“最難的活,要敢接;最臟的活,要肯接;別人不愿意接的活,都要接。人的本領,是在不斷干活過程中學會的。”這簡單樸實的幾句話,雷杰默默在心中記了一輩子。他專心向師傅學習,苦練機修本領,不到兩年時間,終于迎來了一次有挑戰的“畢業考”。
那一晚,夢鄉中的雷杰被一位老師傅叫醒搶修一臺機器,由于他是那天唯一一位住在廠內的機修師傅,便馬上從床上爬起來挑起了重任,通宵了一晚,將長期跟師傅學習的實戰經驗和在校時刻苦學習的理論知識相結合,他第一次完全獨立成功完成了修理工作,并且謹慎細心的他,又加工了十個產品檢驗是否合格,一切處理妥當,同事們也都已經來上班了。“你修好了?”組長驚訝地問雷杰。得知了事情的全部過程后,組長便催促著雷杰趕快去休息。離開車間的雷杰臉上洋溢著藏不住的喜悅,也是這時候,他真正體會到了師傅的那句“人的本領,是在不斷干活過程中學會的。”
車間主任自然將雷杰的進步看在眼中,便將他調到了車間技術組,當車間工藝技術員,管理車間加工工藝,以及加工刀具、夾具、工具等工藝裝備。而這,也正是他漫長的縫紉機事業的開端。
車間加工工藝,是車間技術工作的核心,不僅要了解加工產品的質量要求,還要了解產品在加工過程中的加工設備、加工工藝,加工用的刀具、夾具、工具、量具等工藝裝備狀態。要求工藝技術員的知識面寬,實際工作經驗豐富,問題處理能力強。
那時,只要是廠里的人都知道,什么都能停,就是生產不能停,所以跟機器有關的事,都是大事。
雷杰回憶說:有一天快下班的時候,一把加工車殼的導架槽的銑刀壞了,倉庫也沒有備貨,工具科便連夜趕工,趕出了兩把銑刀。但當第二天早晨把刀具旋到設備上一試,卻發現刀具的螺紋標準不一樣,設備上是公制的,做出來的新銑刀卻是英制的。之前雷杰做機修時,每次深夜修完機器,總會再加工十個產品檢驗是否合格,顯然,這次工具科的同事在工作上并沒有這么嚴謹。
在旁人看來,這是一次“失誤”,或者說是不夠細心,但在雷杰看來,作為源頭的圖紙管理可能出了大問題。在詳細整理信息后他發現,車間和工具科用的刀具及設備的螺紋標準混亂,有公制的、也有英制的。如果每次加工刀具前都要確認好標準,那還不如就從源頭把刀具圖標準統一,解決生產難題,保證生產效率。
雷杰便從整個車間的所有刀具圖紙著手,將過去6套不同版本的刀具圖,統一更新為親自重新繪制矯正過的全新版本,并同時重新繪制了車間全部工藝文件的全新版本。
這次 “刀具事件”給雷杰帶來了很大影響,“圖紙管理”的概念也跟隨他到了每一個工作崗位。
因為工作努力且出色,雷杰很快被提拔為廠技術科副科長,仍主管工藝。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于是他一上任便大刀闊斧地對全廠1379道工序進行了標準化校正。他自己主起草工藝文件標準圖,發動了全廠8個車間的所有工藝員,耗時整整兩年,最終創作完成了1379版協昌縫紉機廠的工藝文件。這套工藝文件,直到協昌縫紉機廠2000年后停產前仍在使用。
當時身為廠里主管產品、工藝、標準、信息、檔案技術工作負責人的雷杰已經深深明白,縫紉機產業既是勞動密集型的,又是技術密集型的,沒有標準化的管理,這兩種特征都會受到限制。
當時許多縫紉機廠采用的管理模式都是傳統的作坊式,其一大特征就是生產技術資料基本都是靠老師傅經驗總結歸納出的一些文字資料、技術資料,這些寶貴的財富如同未經雕琢的璞玉,經過規范的技術管理整理后,才能展現出它們真正耀眼的光芒。
從上世紀90年代一直到2010年之后,雷杰連續擔任全國縫紉機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副主任、顧問。全國縫紉機標準化中心2006年所使用的《縫紉機術語》文件中,主要起草人之一也是雷杰。
1973年,“當時全國輕工部研發縫紉機底板加工組合機床自動線,主要的技術支持是大連組合機床研究所,那里能夠接觸到前蘇聯留下的一套很完整的機床設計的標準化手冊,這對于大部分技術員來說,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這項工作本來安排車間另一個老工程師去參加,但后來他身體欠佳,車間便安排了我去參加設計。”
“當時全國總共有機殼、車殼、底板加工三條自動線同時開始研發,結果,其他兩條線失敗了,其實是因為一開始設計理念有問題,所以我感覺自己的機遇比較好。”
“1983年,上海工業縫紉機廠有一個國家經委批準的引進日本‘高速平縫機產品技術及加工設備’項目。公司領導調我去擔任這個全國最大的縫紉機項目負責人,1984年后公司領導決定任命我為上海工業縫紉機廠廠長。當時廠長的選拔,是根據鄧小平同志的專業化、革命化、年輕化這三個標準進行的,我正好占了年輕化的優勢,所以從一個技術員、工程師開始,被提拔成為廠長也是我的機遇好。”
雷杰在講述自己每個人生階段的經歷時,總是提到“機遇”二字,但事實上,哪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機遇的背后其實都是天道酬勤的結果。
1973年在參與縫紉機底板加工自動線項目時,雷杰延續著自己對于標準化的堅持.由于項目非常龐大,全國有七個廠的工程師、老師傅都參與了進來,他為了盡可能減少誤差,所有圖紙都要親自校對,那時的鉛筆圖紙修改起來也非常麻煩,有時候擦掉修改還不如直接自己重畫,但他依然沒有放棄,從始至終以嚴謹的態度用整整一年的時間完成了自動線的設計工作。
1974年設計工作完成,設計組解散后,全套圖紙就被送到了生產單位,由雷杰一個人在生產工廠主持自動線試制的技術服務工作,1975年自動線制造完成拉到縫紉機二廠,也由雷杰主持安裝調試。1976年1月由于長期在自動線安裝調試,埋頭在車間近半年沒有離開工廠,再加上之前的長時間高強度工作埋下的隱患,雷杰突然胃大出血,被送進了醫院搶救,醫生的一句話讓周圍所有人很震驚了——做好心理準備,可能是胃癌。
“如果確認是胃癌,趕緊幫我處理一下,讓我出去,這樣我最后還能再處理一點事情,換一個人過去什么都不知道,等于又要重新開始了。”雷杰在被送進醫院前不久,調試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問題,他當時滿腦子還都是自動線的數字。但醫生說什么也不讓他走,因為這其實是雷杰第二次胃出血了。
雷杰只得老老實實在醫院待了一個月,好在最后排除了胃癌的可能,這才正式出院。后來的調試工作強度并不高,雷杰的身體也在這個階段得到了適當的休養。
1977年5月,輕工部前來工廠驗收項目,一次性通過。1978年“縫紉機底板加工組合機床自動線”項目還獲得全國第一次科學大會重大科技成果獎。
時任工業縫紉機廠廠長的雷杰已經38歲了,但是跟身邊50多歲的副廠長、老廠長相比,自己還是年輕的小伙子。至于他的專業水平,也是靠先前一點一滴積累出來的。
那時候的雷杰,常常留戀在縫紉機二廠工作的情景,沒有所謂的上班和下班,單身的他住在工廠、吃在工廠,有時甚至三個月、半年都不會離開工廠,并且,他很享受下班后一個人在車間的時光。沒有其他工作的影響,一個人就在空無一人的車間里,一個尺寸一個尺寸地校對,一個文件一個文件地修改。
正是這些勤奮、用心,為雷杰打下了扎實的專業基礎。后來去日本考察時,他與日本重機公司的談判,一談就是一個月,從產品討論到工藝,又從工藝討論到設備,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為后續談判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為我國的縫紉機行業爭了口氣。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用這八個字來形容雷杰再合適不過了。他在談話中間總是強調,跟他能力相當或是比他能力更強的同輩大有人在,但自己正因為有較好的機遇,才放大了自己的勤奮,收獲到了更多的成果。
從1983年開始,前前后后因為技術談判、設備驗收、組織考察等等事因,雷杰一共去了日本5次,每一次去,對他而言都是一次震撼。
他是這樣描述的:“他們的工廠雖然很小,但是管理得井井有條。比如說,重機大田原工廠的老廠長,現在已是重機公司的元老。在1938年工廠剛建立時,作為廠長的他,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檢查廁所是否干凈,因為如果連廁所都干凈了,工廠其他地方自然就不必再檢查了。檢查完廁所之后,他便會拿起掃帚親自打掃工廠門口的十字馬路,掃完后再穿著白襯衫橫躺在馬路上,一直掃到白襯衫上不會染上任何灰塵為止。”
他感嘆道:“日本同行在細節方面真是做得很好,他們的廠長以身作則這件事情也確實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來在工廠管理方面也給了我許多啟發。”
反觀國內,數十年來高速發展,行業保持著瞬息萬變、日新月異的迅猛勢頭,這確實是好事,但每經過一些階段,我們是否需要回首?是否需要從過去的路程中自省?不管是對于標準化的堅持,還是吃苦耐勞的精神,不知為何都在我們行業慢慢強大的路上逐漸弱化了。
現在看行業的發展,其實欠缺的是擁有心懷家國情懷、系統性發展的概念,以及整個行業發展的概念。七宗罪是西方傳來的說法,其中一罪便是貪婪,確實,人要戒貪是件難事,但這也是達成高質量發展必須要做的事。
“現在的人都好浮躁,我不希望大家總是在空中。我們這個行業現在真正需要好好沉下心來去討論,什么叫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