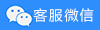兄弟brother,出現故障代碼Err-100,



圖:衣拿智慧產業園
人生真是奇妙而無常,充滿了無限可能。
2003年的時候,40歲出頭的翁端文還是東南亞一位成功的縫制設備經銷商。
圖:浙江衣拿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翁端文董事長
當時,他剛從亞洲金融風暴的洗禮中走出,面對人生中重要十字路口的抉擇:是繼續待在印尼還是走出去?是繼續做代理還是找到一個新的事業方向?
他當時已經有意投身于制造業,但是去做縫紉機還是其它什么產品,他一直猶豫未決,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種名叫“吊掛”的自動化設備。
抉擇往往是痛苦的,因為它考驗的是一個人的眼光和勇氣。
那時候,吊掛還是新鮮事物,最早由瑞典銥騰于1964年發明,后來加拿大也于1978年開發了自己的系統。正是在現場親眼目睹了吊掛演示之后,翁端文才認定自己找到了未來的方向。基于對縫制設備和服裝產業發展的深刻洞察,他看到了吊掛的未來,以及它在未來能夠產生的價值。
圖:羅萊家紡 赫岱斯智能吊掛系統
他趁加拿大衣拿(INA)業績下滑的時機買下其軟件系統,又從美國買了整個機械結構,開始在印尼嘗試做全自動吊掛。但是因為印尼輕工業基礎薄弱,缺乏精密加工企業,供應鏈整合非常艱難。
在這種情況下,翁端文將視野投向剛剛入世的中國大陸。2003年,他到中國考察,廣東、福建、上海走了一圈,找了幾家縫紉機廠談合作。但當時很多老板看不懂吊掛,也看不到它的未來前景。直到翁端文遇到了飛躍董事長邱繼寶。
那是2003年年底,翁端文去臺州拜訪邱董,本來想幫他賣繡花機,但是已有另一家代理商捷足先登。邱繼寶感覺很不好意思,就陪翁端文乘飛機到上海。只有35分鐘的行程。
路上他跟翁端文的助理坐在一起,閑聊時隨口問了一句:“你們老板常來中國,是想做什么生意嗎?”
助理告訴他:老板來中國想設廠做吊掛,或者找個合作伙伴一起做。”邱繼寶在簡單了解了什么是吊掛后,說“我有興趣啊”,馬上請助理跟翁老板換座位。倆人聊了不到10分鐘,飛機就降落了。他們在機場又繼續聊,并約定過幾天后正式簽約。
翁端文記得很清楚,那是2003年12月24號,圣誕節前一天。他跟邱繼寶握了個手之后就飛回新加坡。幾天之后的2004年1月3日,他又飛回上海,去臺州跟飛躍正式簽訂了合作協議。
機緣巧合之下,兩個看得見未來的人走到一起,并由此推動了吊掛行業在中國市場的萌芽和發展。志同道合的人往往都惺惺相惜。翁端文和邱繼寶都是這樣的商界英才。
翁端文1961年出生于新加坡,父親是縫紉機修理工。他16歲就開始修縫紉機,21歲退伍后做了幾年機修。1986年,在看到經銷商的利潤空間之后,他成為銀箭品牌代理商。第二年,因為美國取消針對亞洲“四小龍”的優惠外貿政策,他轉戰到印度尼西亞。接下來,以印尼為基地,他經銷的品牌涉及中國、日本、瑞士、意大利等國,市場覆蓋了中國大陸、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尼和新加坡等國。在印尼的十年,是他賺到人生第一桶金的十年。
從2004年開始,翁端文將事業重心放到中國大陸,專注于吊掛。與縫紉機行業的競爭激烈性相比,他認為吊掛的產品生命周期更長,至少十年內不會出現強有力的競爭者,而且可拓展空間更大。
然而萬事開頭難。2004-2006年,是衣拿吊掛在中國大陸市場的播種期。
衣拿在中國的第一家客戶,是常州一家服裝廠。那還是在2003年,服裝企業對吊掛還很陌生,大多數看不懂也聽不懂,很多老板比較排斥,即使先安裝給他們試用都不要。翁端文至今仍感念那家常州企業給了衣拿機會,使其有了一個推廣吊掛系統的良好開端。
一直到了2010年至2012年,才是一個真正的拓展期。“我們到全國各地去拓展,到海外去拓展,其實當時國內外已經在賣了。”
2013年,隨著國務院《關于推進物聯網有序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發布,一直到2015年都是物聯網概念的蓬勃發展期。盡管直到最近三五年物聯網才真正實現落地應用,但當時衣拿吊掛從前端的集中裁片到后端的整燙包裝,都已融入了物聯網概念。
也正因為衣拿與時俱進跟上了物聯網潮流,才有了2014年來自報喜鳥的訂單。翁端文說,“當時紅領集團是全國第一家把整個數據打通的服裝企業,但是物流還沒打通。報喜鳥找到我們,要求把信息和物流都打通,做智能化定制。后來我們又為贏家女裝等一大批服裝企業做定制,當時衣拿在智能化定制領域基本上占了70%的市場份額。”
圖:紅豆集團 衣拿云物聯吊掛系統7RTS
從2016年開始,大數據浪潮又撲面而來。當時的潮流引領者是阿里的犀牛工廠,衣拿也參與其中。這個項目于2017年8月在阿里內部啟動,秘密運營兩年,把數據真正應用在制造環節中。“很多客戶的需求慢慢變成不是追求產能,也不是追求吊掛,而是追求數據呈現。”所以這段時期,被翁端文定義為衣拿的數據期。
圖:阿里犀牛新制造工廠 衣拿棋盤式吊掛系統
到了2019年之后,對衣拿而言是一個跨行期。因為疫情的爆發,對服裝產業造成一定沖擊,衣拿也受到很大影響。比如貨運到海外,要么工廠沒員工,要么不肯清關;在國內,很多客戶因為疫情不能安裝,即使安裝好了沒有員工,等有了員工又沒法培訓——這一連串的挑戰,迫使衣拿尋求跨行業發展,在服裝企業之外的應用場景做了更多嘗試,將吊掛生意延伸到了商超、電商新零售、外賣新餐飲、醫藥、汽車相關和物流運輸等其它領域。
衣拿一直致力于不斷改善自己的產品,在確保質量穩定的同時,融入更多的創新科技。在今年CISMA2021期間,衣拿展出的融入了云技術、5G技術、視覺技術的新一代吊掛系統吸引了眾多客戶的目光。翁端文說,未來衣拿還會將更多的創新技術,如AI和新一代智能算法融入到吊掛系統中。
衣拿在中國18年的升級進化,一方面充分享受到了服裝產業飛速成長、轉型升級的時代紅利;另一方面也通過辛勤的市場培育和緊跟市場需求,專注于創新,專心于深耕,實現了對吊掛細分行業的引領和自我超越。
作為一個毫無爭議的拓荒者和引領者,衣拿還帶動了一大批國內民營吊掛企業的成長和發展,行業規模也越滾越大。
韌性是企業家精神的底色。
尤其是當下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寒氣襲人的時間節點,更需要企業家事先做好抗風險的充分準備,以應對大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
作為亞洲金融風暴的受害者和親歷者,翁端文對潛在風險有著天然的敬畏。他將2022年視為衣拿的挑戰期。疫情疊加俄烏戰爭導致全球性的消費疲軟,在他看來或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真正挑戰。
去年衣拿新廠房裝修,翁端文眼看著形勢不對,果斷砍掉了3000多萬元開支,能簡則簡,一減再減,為有質量地“活下去”未雨綢繆。
他說,因為之前經歷過金融海嘯的沖擊,一個非常重要的感悟就是“寧可信其有”。只有相信了事情會發生,才能做好事先的應對,同時在心態和思維上做好承壓準備。這個感悟,是他用血淋淋的教訓換來的。
1998年,金融海嘯席卷東南亞,翁端文所在的印度尼西亞也未能幸免。他說那一關其實完全是可以避開的。當時他以極優惠利率從世界銀行借了一筆美元,到時候結算的時候,要以匯率用印尼盾兌換美元去支付。
風暴初期,匯率已從一美元兌2400印尼盾,跌到一美元兌5000印尼盾,當時銀行的人跟他講,讓他趕快去鎖定匯率,以規避下跌風險。翁端文想當然地以為,既然已經跌一倍了,應該再跌也不會跌太多。
“結果最后跌到多少?17200。從2400印尼盾一直跌到17200。我一夜之間什么都沒了。這是給我的一個很大的教訓。”
為了給銀行還債,翁端文把60多輛汽車全部出手,把所有不動產,包括廠房、倉庫,海邊的兩座大別墅,還有十多間公寓,所有的店鋪等等統統拋售。那時候內心里所有的掙扎和痛苦,也只有他自己才能去體會和品味。
1998年底他重新站起來,依靠供應商的大力支持,花了兩年時間,把在印尼賺了10年虧掉的錢,又都賺了回來。從哪里跌倒,再從哪里站起來。
但從此之后,翁端文對市場的變化異常敏銳,對專業人士、銀行家和大企業家的觀點非常關注,敬畏風險,敬畏專業,凡事寧可信其有。
因此,當去年年底覺察到一些用厚料的家紡、家居企業業務量開始下滑,再加上一些大企業開始裁員、緊縮的時候,翁端文就意識到接下來的市場會疲軟。他預感到未來無論是經濟還是行業,可能會產生比較大的變化。因此他從去年底開始就大幅縮減開支,降本增效,對員工進行風險教育,提早“御寒”。
“我從去年就感到有一點‘寒’,但是沒想到現在是那么‘寒’。”翁端文正密切關注疫情和俄烏戰爭的變化,尤其是戰爭的影響,導致來自歐美的訂單大幅下滑,再加上因地緣政治引發的能源供應問題,也影響歐洲很多工業國的產能和需求,這將是一個惡性循環。
按照西方的“墨菲定律”,可以推導出一個極端表述:如果有壞事可能發生,不管這種可能性有多小,它總會發生,并造成最大可能的破壞。這其實也就是翁端文所感悟到的“寧可信其有”。
他說,“我預見到的春天可能會在2025,我把2025年當成是笑臉的一年” 。
未來并不可知,但也并不可怕。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自然有自然的規律,周期自有周期的運行。為了迎接2025年的笑臉,需要先調整戰略以應對市場變化。
挑戰其實遠遠不止疫情和戰爭所帶來的那些困擾。
吊掛這個行業發展到今天,就像翁端文和邱繼寶在18年前所預見的那樣,已經呈現出使用普及化、競爭白熱化和整廠集成化的特征。接下來行業如何發展、產品如何創新,關系到全球7億的市場規模能否再上一個新臺階。
如果行業未來出現類似縫制設備一樣的價格戰,而行業頭部企業又沒有足夠的凈利潤來支撐研發的話,就必然會走入一個抄襲模仿的老路,其結果也就很難在吊掛領域出現新的突破和新的創新。
在過去幾年,衣拿投入在研發領域的資金始終保持在六點幾的水平,今年市場下滑、前景黯淡,翁端文卻大膽地將研發投入調高到8%。
他說,現在的挑戰已經不是一個行業競爭的概念,而是吊掛如何更好地與物聯網融合,如何更好地與大數據、AI、智能算法進行集成。創新進入深水區,不進則退。
“我常跟客戶講,首先我們衣拿做的就是把物流打通,然后再把信息化打通,因為物流打通之后,所有的數據采集才能在MES系統中支持或接受指令,然后再反映到ERP的管理上,這是一個過程,之后才能談到生產布局合理化,才能產生更大的效益。”
與大多數同行不同的是,衣拿擁有自己的MES系統,擁有自己的ERP子公司,擁有更廣泛的與第三方軟件供應商如SAP、甲骨文等的深度合作——能夠把全流程的數據打通,這是衣拿的強項。
同時,它的向上兼容能力和定制能力,又確保其在售賣吊掛產品之外,還能提供更多增值服務以及一站式整廠規劃解決方案。
它的服務內容,包含從前期的客戶現場調研、方案規劃到系統安裝,再到后期的精益生產管理培訓、長期維護保養;而一站式解決方案,則包含前后道一體化,智能后道及倉儲系統,以及智能單機和貫穿全流程的軟件系統。
翁端文說,為快速響應市場變化、創新產品服務和增強持續迭代優化能力,衣拿積極推動業務模式轉型,組建了專門團隊負責吊掛系統的專項開發,還成立了行業拓展部,負責電商新零售等新行業空中物流項目;新智造團隊,負責物流、AGV;智能單元機團隊,解決行業痛點問題;精益生產管理培訓團隊,負責為客戶提供優質的顧問培訓服務。
“新拓展的這些產品,都是和我們吊掛產品有緊密的聯系,是對吊掛產品的一種補充和完善,使客戶在使用衣拿吊掛提高傳遞效率的同時,同步解決其它痛點,并提高配套工序的效率,這樣讓客戶最大化地感受到吊掛系統帶來的智能化體驗。”
以智能空中物流為例。這是衣拿近幾年來非常專心、專注的一個新領域。“空中物流能夠做到點對點,經過篩選、配對加上管理,產能可以提高20%-30%,這已經是被很多客戶體會和驗證過了的”。
衣拿服務過一個客戶九州通,主營醫藥物流,在全國約有兩三百座倉庫,原本是藥品放在貨架上,需要人工去每一個貨架取藥,導致效率不高。衣拿提供的解決方案是,設計一個空中物流系統,把藥品放進一個空中載具,訂單需求什么,一鍵導入它就能自動篩選、自動配對、自動輸送,實現藥到人取。
這套系統不僅可以提高效率(可減少75%的人工),做到最大限度的空間利用,而且最重要的是確保了物品分揀的準確性。無論是藥品還是商品,如果靠人工去看去分揀,難免會出現錯誤,因為這跟人每天的狀態有關;但是智慧物流設備不會有這個問題,所以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空間瓶頸、投入能力和分揀錯誤的問題,客戶滿意度也在不斷提升。
對大多數客戶來說,他們最關心的是能真正解決他們的痛點,而且解決方案還能真正落地。最近衣拿跟安踏合作,后者的痛點是在生產過程中,如何把輔料分配得更合理,如何保障及時供應,如何做到供應數量準確無誤,如何在打通數據后實現軟硬件的配合,如何解決濕度問題等等。
翁端文說,比如解決濕度問題,當然需要烘干機,以前廠家都是找第三方或第四方配合,且需要人工操作。而衣拿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吊掛直接從烘干機里走出來,不需要人工。除塵機也一樣。羽絨服除塵,通常是依靠人力手工除塵,衣拿則設計吊掛直接進除塵機,解決了運輸、搬運、數據和品質問題。
還有拍絨環節。生產羽絨服時需要拍絨,但拍絨機對不同產品有不同的拍絨要求,而且面料有軟有硬,拍得不好的話,會造成損傷,還會把羽絨拍得左右不均。為解決這些痛點,衣拿開發了智能拍絨除絨機,并結合AGV設計出了跨樓層的運輸方案。此外,因為客戶廠房超過一萬多平方米,衣拿還幫它設計了空中巡檢機器人,方便巡查每一個角落,節省了大量人力。
衣拿的實踐告訴我們,只要客戶的需求永無止境,產品的創新就永不停步。而且正像現實所告訴我們的,吊掛在中國成長發展到今天,已經迫切需要一個全新的改革。
翁端文舉了一個例子。比如阿里巴巴的犀牛工廠,是衣拿負責做的整廠物聯解決方案。“吊掛本來是一條線一個站的概念,但如果有10條線500個站,如何建在一起?這是一個全新的挑戰。最終我們做了一個多層立體吊掛,也就是說,空中有10條線,有立交橋有橫跨,還有前后對接,所以各個角落各個方位需要加入到這道工序的話,它就以最快的途徑,以最短的時間,找到這臺機器來加工。這將是未來的一個發展趨勢。”
還有一個方向,是做到讓吊掛配搭不同的載具。對服裝行業來說,載具承重一般是1.5公斤,衣拿現在已經把它提升到15公斤,甚至25公斤,這是一個新的改革,其應用領域將非常廣闊。
展望未來,翁端文將衣拿的重點放在兩個方面。一是繼續專心專注于智能空中物流,并盡可能地延伸開去,發掘更多的應用場景。二是帶領團隊更靠近市場端。也就是說,以前是先有產品,再去聚焦市場;而未來衣拿要做的產品,一定是從市場端、需求端發掘出來的。對他來說,吊掛不是一件商品,而是一件產品。因為商品是已經制造完成的東西,而產品則還要根據客戶需求、場景要求以及實際落地的要素,作進一步的設計和完善。
60多歲的翁端文已經過了耳順之年,但跟他多次交談,總能感受到一種強烈的進取心和前瞻意識,企業家精神于他而言,就是毅力、信念和對吊掛事業的摯愛。
文章寫到最后,突然想到一句話:
別低估了眼界和方向的威力,這些不可阻抑的力量能夠改變看似無法克服的阻礙,使之化為可穿越的小徑和擴展中的機會。
心在,機會就在。縱然前途渺茫,縱然未來暗淡,但就像電影《至暗時刻》片尾那句話所說的:
If you are going through hell,keep going. 縱然經歷煉獄,只要一直往前,就能走出去。路和希望,都在我們腳下。